想你到大海:百年前未完成的懸念,來到了雨水的盡頭 | 如何做好生意 - 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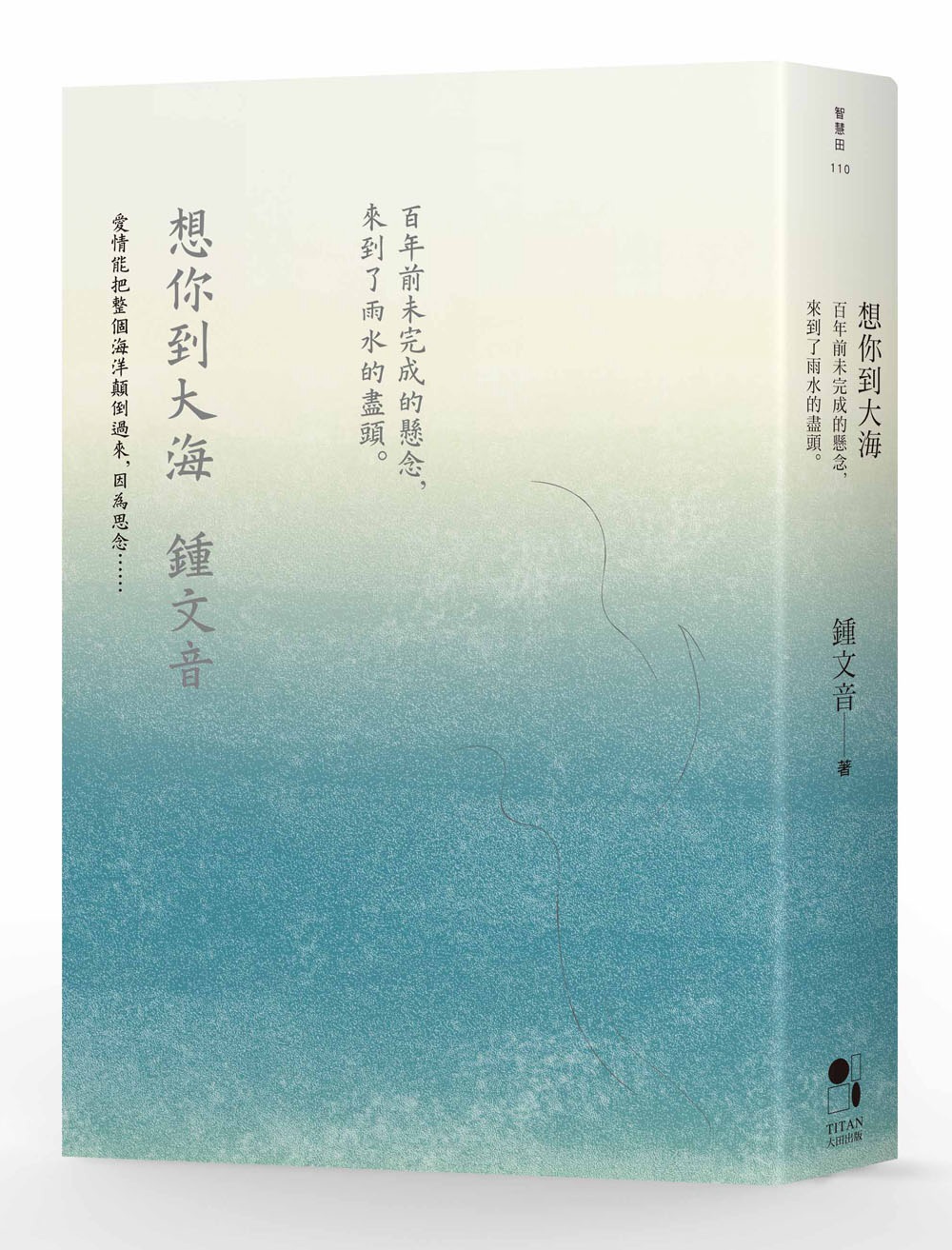
想你到大海:百年前未完成的懸念,來到了雨水的盡頭
愛情能把整個海洋顛倒過來,因為思念……
小說之神眷顧的靈魂 鍾文音長篇史詩
這些生命是我個人雲遊他方的夢境。
是時間,也是故事。是歷史,也是個人。__鍾文音
青春的淡江女孩與百年前的夢婆,相逢在「我們的海」。
「我們的海」是一間異鄉人暫居的旅店,他不只收容了現下逃離異地的憂傷靈魂,更收容了百年前飄移不定的鬼魅,人與人的相遇,或者人與夢的交織,不是時空問題,而是心的感應。
在這個世界,每個人都是異鄉人,即使人在他方,卻有可能改變歷史、改變際遇,不論是來到福爾摩沙的傳道者馬偕,或是游移於情感訊號的淡江女孩。
鍾文音以「當代米妮」疊映「島嶼妻」與「夢婆」,靈與靈之間的對話,繁衍一場青春與信仰的苦痛抵擋,大河史詩般的交疊講述,幾乎顛覆一座海洋。
七年執筆完成,小說家企圖心滿滿,一貫風格的文字密度,本書達到高峰,獨有的敘事結構 ,真正體現的是任何時刻,任何地域,深海夜空下不安份的殤情慾動。
作者簡介
鍾文音
淡江大傳系畢,曾赴紐約習畫。專職寫作,以小說和散文為主,兼擅攝影,並以繪畫修身。一個人周遊列國多年,曾參與台灣東華、愛荷華、柏林、聖塔菲、香港等大學之國際作家駐村計畫,講授創作等課程。
曾獲中時、聯合報、吳三連等國內重要文學獎。二OO六以《豔歌行》獲(開卷)中文創作十大好書。已出版《一天兩個人》《少女老樣子》等多部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與長篇小說等,質量兼具,筆耕不輟。小說《在河左岸》改編成三十集電視劇,深受好評。
二O一一年出版百萬字鉅作:台灣島嶼三部曲《豔歌行》《短歌行》《傷歌行》,並已出版簡體版、日文版與英文版。
最新散文集《憂傷向誰傾訴》《最後的情人》《捨不得不見你》。
鍾文音網站:wenyin.uright.com.tw/
鍾文音FB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714512502
異鄉人交織拼貼一個幻化世界。
這個世界有人情「世」故,有邊「界」移動,
有古代有現代,有大海有高原,
有城市有山林,有酷暑有雪獄,
有繁華有荒涼,有婚配有寡居,
有逸樂有救贖,有獲得有失落,
有掠奪有給予,有和解有仇恨,
有不思善有不思惡,有光亮有黑暗。
他們其實也是鏡中之我……
008【序 曲】維若妮卡的手帕 雙面米妮
【卷 壹】諸神的航線
012 一 在雨水的盡頭
066 二 我把大海寄給你
097 三 尋找者的國度
135 四 解碼者
【卷 貳】島嶼複音
176 五 當他們出發時
237 六 一滴大海
283 七 變遷與哀傷的海
305 八 與海比老
【卷 叁】金星以南 未曾走過的路
328 九 走水路 航向我的男人之邦
365 十 走陸路 踩踏新世界的女人
【卷 肆】在愛苦之海
376 十一 一生最後的住家
401 十二 山魚水雁
【卷 伍】老神寡婦
418 十三 海不枯石不爛
465 十四 沿著貓路的河
496【後 記】命運交織的抵達及其神祕
後記
命運交織的抵達及其神祕
直到我旅行異鄉多年之後,我才看到我的淡水是一座如此混雜著異鄉情調的多雨小鎮。
在我就讀淡江時,人生交織的只有知識與愛情,沒有家族沒有歷史,青春生命活得彷彿無身世的人,直到青春燃盡,才看見每個人都是故事的繼承者,歷史的建構者。
淡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地景:第一次離家,第一場愛情,第一回遊河。但離開大學城之後,我即離開淡水,除了短暫幾年曾在台北工作外,我一直在路上。
自此故里與異鄉這兩條交錯列車不斷地擦撞著我的生命板塊,我遇過無數的異鄉人,遭逢無數人與人的故事,高原平原冰原草原……地景如列車上不斷退後的模糊風景,最後自己也成了故里的異鄉人,異鄉的陌生人,列隊的失語者,時光的背對者。所到之處是異鄉,往事也是異鄉。
往事如異鄉。
生命的異域,感情的異地,錯置的靈魂,如雪絮飄飛,如鏡面倒映。
返鄉的異鄉人
離鄉多年之後,我又住回了淡水河沿岸,沿河而居的生活對撞著異鄉旅途,總使我想起無數異鄉人的臉孔,異鄉人在故里與異地發生的際遇。這和我過去書寫的旅行系列不同的是,我過去的旅行書寫僅關注在我自己的當下旅程與我心儀的藝術家故事的彼此對撞,旅行時空並未拉大,自我的歷史也沒有參與進來,當然也不曾將島嶼重新安置在「異鄉人」的歷史與目光之中。
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怨懟街〉也從淡水出發,以淡江墮落街為原型的愛情小說,但小說裡看不見淡水的歷史,只餘個體的青春哀歡。早期曾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怨懟街〉,多年後,連綿延展擴大成三十多萬字的《想你到大海:百年前未完成的懸念,來到了雨水的盡頭》。
一八六○年,一只條約讓淡水開埠,一個女孩從此出生。一八七二年,一個傳道者上岸島嶼,這一年童養媳女孩的小丈夫過世,歷史轉彎,他們等著相遇。我開始對歷史有了想像的熱情(雖然自我的生命故事依然纏綿不休)……
雨水的盡頭—滬尾,這樣詩意的名字,常使我想起多年前那個剛剛離開母親的女孩,爬著克難坡或者徒步走到海邊的青春歲月,這多雨潮濕的小鎮,讓女孩多次佇立碼頭望著渡輪送往迎來。在紅毛城與教堂或者砲台埔拍下大學畢業照時,我只知道有一天我要離開這座海,迎向我的新世界,我要乘海離鄉,這一離多年,直到近年母親中風倒下,親情把我的雙腳牢牢釘在島嶼,且如此地靠近我的青春之城。
母親成了病人,長期往返淡水竹圍馬偕院區。
當這本小說還在修改的路上時,母親卻已然住進了小說人物的現場。
今昔對照的命運
我總覺得是小說之神將母親召喚到馬偕醫院的,因為我動筆寫《想你到大海》大約已是七年前的事了,靠近馬偕醫院後,使我更有感於當初一個異鄉人提著醫藥箱和聖經上岸的歷程,但人物故事已然被神化和刻板化,使我寫起來非常綁手綁腳。於是最後我用一種既熟悉(畢竟我從十八歲起就在這條河流生活,從淡江女孩到淡江一姊)又陌生(歷史通過陌生化的眼光再次給予新的敘述),比如書寫首次從島嶼出發海陸旅行世界的張聰明的「旅行筆記」,旅行筆記的擬仿之音,其實也是作者旅程的魅影幽魂再現。
很多年後,當我從世界歸來島嶼,我才驚訝地發現自我過往的旅程無形中覆轍交織著張聰明的旅程,她的旅程如此堅貞,和我是如此地不同。小說原本寫四十二萬字,最後我把自我的旅程剪去,只獨獨留下張聰明的旅程書寫,以一個「擬仿」的我,書寫張聰明的旅程心情,以一種「筆記」體,去假想她的旅程所見所聞。當然小說是一種虛構,建構現實的旅程之下,她的所見所思當然是作者的「再造」。因而小說裡多以「傳道者」「島嶼妻」稱之,人物採集自歷史,但已演化成小說。小說出現的當代外國旅人名字,都是過去曾經到過淡水的異鄉人,將過去與現代重疊,賦予歷史幽魂新的復活。重新對異鄉人探勘,把他們還原成遊子,來到島嶼開天闢地的想像書寫,以心境的描述來對應際遇的荒謬性。
小說兩條主線,一是以淡水旅店「我們的海」的章米妮為主敘述(以張聰明護照上的英文名字Minnie為對照組,使今昔淡水女孩的樣貌呈現劇烈的差異,兩個不同時代的米妮映照出時間的軸線)。章米妮在淡水繼承祖父輩這間老旅店,同時當解說員地陪,以此帶出另一條傳道者與島嶼妻的歷史敘述。串聯這兩條主線的是島嶼不死的靈魂「夢婆」,只要米妮一靠近夢枕,夢婆就會傳輸文字給她,夢婆無性別,他是一個敘述者。小說通過夢婆「轉述」「轉印」,又多了小說歷史的曖昧性與不確定性。
抵達的神祕與荒涼
我且刪掉了母親住院馬偕的種種過程,因為這是我的下一本長篇小說《帶你上高原》書寫的起源,一個女孩為了母親的送終之旅,抵達高原的種種際遇與變化。
換言之,異鄉人系列已然成形。
我的下一本小說也已經在動筆了,將再轉換地景,由大海來到充滿轉山生死隱喻的高原。島嶼迎來異鄉人,異鄉人離開島嶼。文明交會,際遇交會,熟悉與陌生交會,故里與他鄉交會,現實與虛構交會。
如此產生了新的系列書寫,觀看事物也有了新的方式。在一座移民混血之島,不可忽視的多元文化與種族,領著我朝異鄉人的複雜性走去。我的寫作生涯一直都在島嶼,因而這座島嶼注定成為我的出發與抵達的座標。
我的人生又曾經四海雲遊,這個現實也注定了有朝一日,我的旅行觀看不會只是散文書寫,其複雜性與黑暗面勢必要回到小說。身為職業寫作者與半雲遊僧,我無法只寫一個城市一座島嶼。儘管寫異鄉人,是有些壓力,因為我的書寫和當今標榜的旅行浪漫是逆反的。但我認為真正的異鄉人是永遠無法不帶著故里去看世界的,嚴肅的旅者永遠懷著自我也懷有他者,對於歷史與文明保有開放性的探索。
我終其一生都將省思與探勘我的故里與他鄉,同時思索與想像異鄉人是如何改變自己與一個地方的命運。
我們都是天地的旅人,天地供我們借居,天地使我們行走。我們何能自鎖一方?如要解鎖,最先就是得注目自我。然一個無視自我的人將看不懂他者,而一個只視自我的人當然也是無從昂揚他方的。
當我在二○一一年出版島嶼三部曲最終曲《傷歌行》之後,我把目光調回兩個視點:故鄉裡的異鄉人,他鄉裡的故里人。當時提筆想書寫異鄉人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的長篇小說《短歌行》日文譯者上田哲二先生驟逝,一個耕耘台灣文學的日譯者,使我想要以小說來書寫島嶼的異鄉人,但彼時他的故事太靠近筆端,太近而失焦,且靜筆尚未沉澱,於是我把筆墨推向我的淡水,這座曾讓異鄉人在多霧的夜晚思起蘇格蘭祖上鄉愁的小鎮,於今似乎只剩下河岸的燒烤與觀光客了。
在書寫《想你到大海》時,我的母親病房正巧來了印尼看護阿蒂,於是之後我的異鄉人書寫系列,也將擴大至東南亞。
於此時代,科技一個按鍵就把我們帶到世界,但那其實是一個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擬想世界,因為個體看到的螢幕世界,手指一「滑」就成了過眼雲煙。
我以為唯有個體真正踩踏行旅他方,或者真心感知來到自我世界的異鄉人故事,如此才有可能在面臨異文化的同化過程產生對磨合歷程的深刻同理與尊重。
如同我喜愛的作家奈波爾(V. S. Naipaul)所描述的古典世界—那個之所以成就今天的我們,卻已然遭我們遺忘的世界。
我們善於遺忘。
書寫者如我,心中卻常浮現漂泊的旅人,在陌生的城鎮,歷盡滄桑的生命,這些生命是我個人雲遊他方的夢境。是時間,也是故事。是歷史,也是個人。
異鄉人的光芒與黑暗
犀利敏銳的旅行者保羅‧索魯(Paul Theroux)曾說旅人本質上都是樂觀主義者,否則他們絕不會到任何地方去。
在我的異鄉人小說系列第一個上場的異鄉人傳道者即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且還是一個嚴厲的實踐者。因為這樣,他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改變了抵達之地、改變了歷史的發展、改變了在地信仰、改變了中西愛情的可能。這樣的異鄉人,在我心中是複雜的,是極其光芒閃爍的表象之外有其自我的黑暗。
一個傳道者,最終以「失語」,告別雨水的盡頭。
我常常在醫院照顧母親時,想著小說的尾聲隱喻。如此靜默的哀愁。窗外滬尾,卻是如此地喧騰騷動。在充滿藥水味與蜂鳴器不斷響了又靜止的空間,我完成了遲遲因為現實經濟而擱淺多年的《想你到大海》,百年前未完成的懸念是甚麼?小說讀畢,懸念才能終了。
異鄉人在我的筆端交織拼貼成一個小說家獨有的「世界」:有人情「世」故,有邊「界」移動,有古代有現代,有大海有高原,有城市有山林,有酷暑有雪獄,有繁華有荒涼,有婚配有寡居,有逸樂有救贖,有獲得有失落,有掠奪有給予,有和解有仇恨,有不思善有不思惡,有光亮有黑暗。他們其實也是鏡中之我,個體的微型。
這也是抵達之謎,創世記之指即將碰觸,際遇可能一觸即發。我一直著迷一個地方生活著許多來自不同地方的各色人等,不同的面貌與經驗交織交融。彷彿回到唐朝長安城第一次發生異邦文明的華麗大熔爐的進程。
移動帶來新的目光,目光重新折射命運的地圖。於是,舉步即異鄉,異鄉也是同鄉,他鄉也是此鄉。
管理這棟旅店,程序很快熟悉,但困難的是處理各式各樣客人的心情與突發的小細節,各種怪癖的客人,還有客人忘記帶走的物品也幾乎可以寫成一本在旅途的遺失物之書。最怪的客人是曾經忘了拿走義肢,不知他後來是怎麼離開的?還是義肢是用來偽裝的乞討者?掉落最多的就是耳環戒指項鍊等細物或圍巾領帶襪子,刻意留下不帶走的通常都是書籍,尤其旅遊指南書,或者商展介紹之類的書。旅遊指南書在旅行結束後瞬間成廢書,成了旅館書架上最多的書。規模小的旅店缺點就是週日房間不夠,週間卻又顯得房間太多,週日每一間生意都好,週間就靠本事。所以她也在思考著如何擴大海外客源,為此她參加了多倫多旅館與觀光文創營。從訂房入住到旅館補貨,一切都可在網路完成,除了打掃與清潔外。這也是麻煩之處,米妮和附近幾家小旅店聯合聘請以減低單獨請人的壓力,但速度稍慢,讓等待入住的客人有時會抱怨。接手管理我們的海後,她的耳朵已開始習慣長繭,嘴巴開始習慣說對不起、不好意思,微笑再微笑。凝視這間面海的悲喜小旅店,照顧著幾隻老貓與她這間從祖父年代就有的小小旅店,這間在小山坡的面海旅店,每面窗都可以看到海,但因為要爬坡,這使得攜帶行李的客人視為畏途。米妮聽說祖父年代在碼頭還可以付費找搬運工協助扛行李,現在碼頭到處都是觀光客,古老的體力工作顯得如此稀有昂貴。這也使得來到我們的海的旅人多是背包客,她也在網站貼出小山坡石階的照片,提醒將大行李寄放火車站,換成小背包再前來。但仍常見有人提著行李箱在山下打電話要他們旅店的人下去幫忙扛。訂金都收了,這時候真是只能「以客為尊」,即使心裡咒罵著這種奧客,覺得自己付錢就是老大,不看貨不管網站公告的警示圖片與訊息。她的手臂與腳力都被這山坡訓練得很有力了。她的家就是旅館,她最熟悉旅者的寂寞了。一個人入住旅館總是會吸引她的注意,但在我們的海,經常是一個人來入住,或許因為這樣,一個旅人很容易和另一個旅人結伴。因她還頗擅長攝影,所以自接管之後就有了些創意。這裡是她熟悉的淡水,她的青春之城,她當業餘地陪也綽綽有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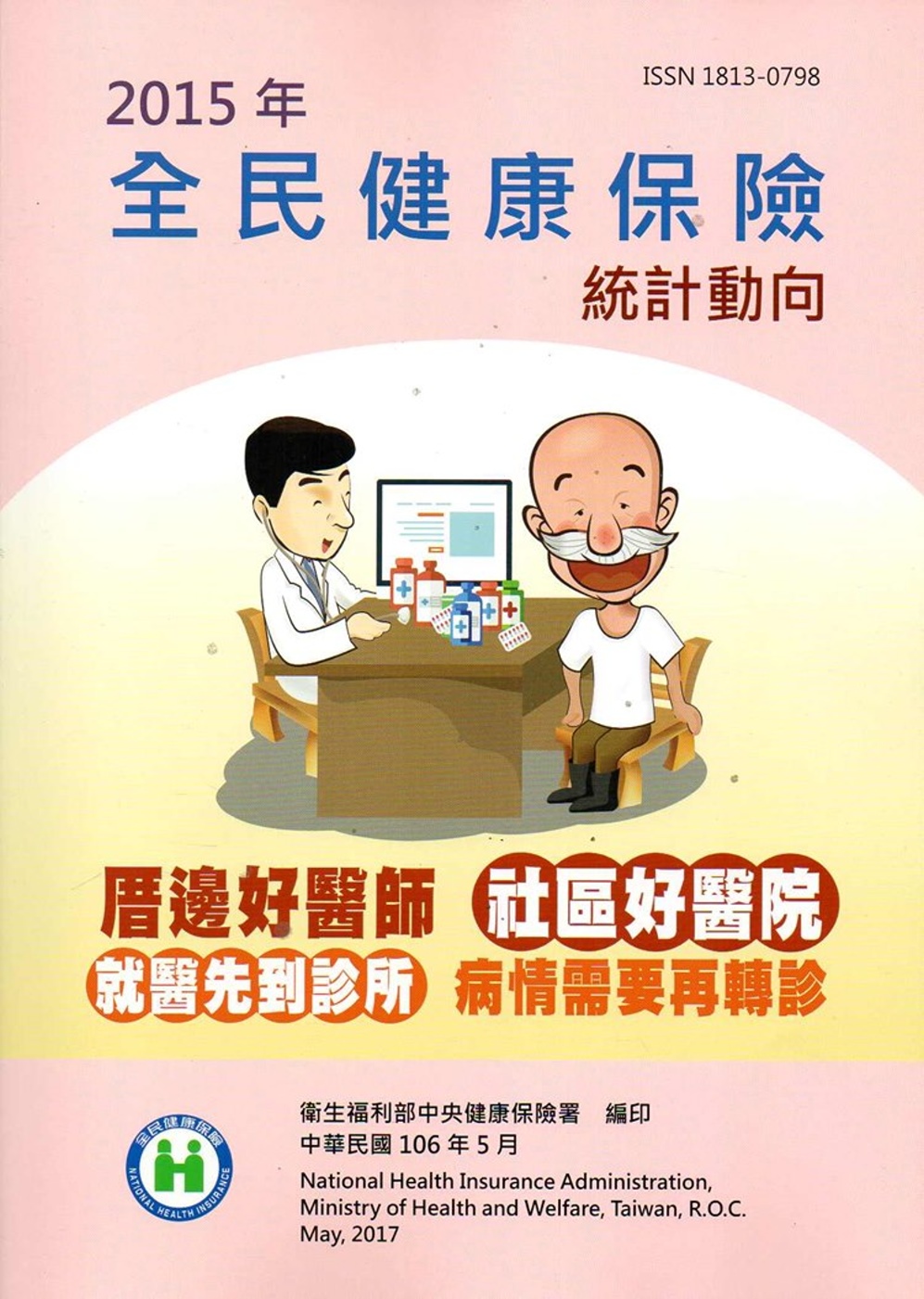 2015年全民健康保險統計動向
2015年全民健康保險統計動向 2020-2021全民健康保險民眾...
2020-2021全民健康保險民眾... 社會健康保險法制之研究
社會健康保險法制之研究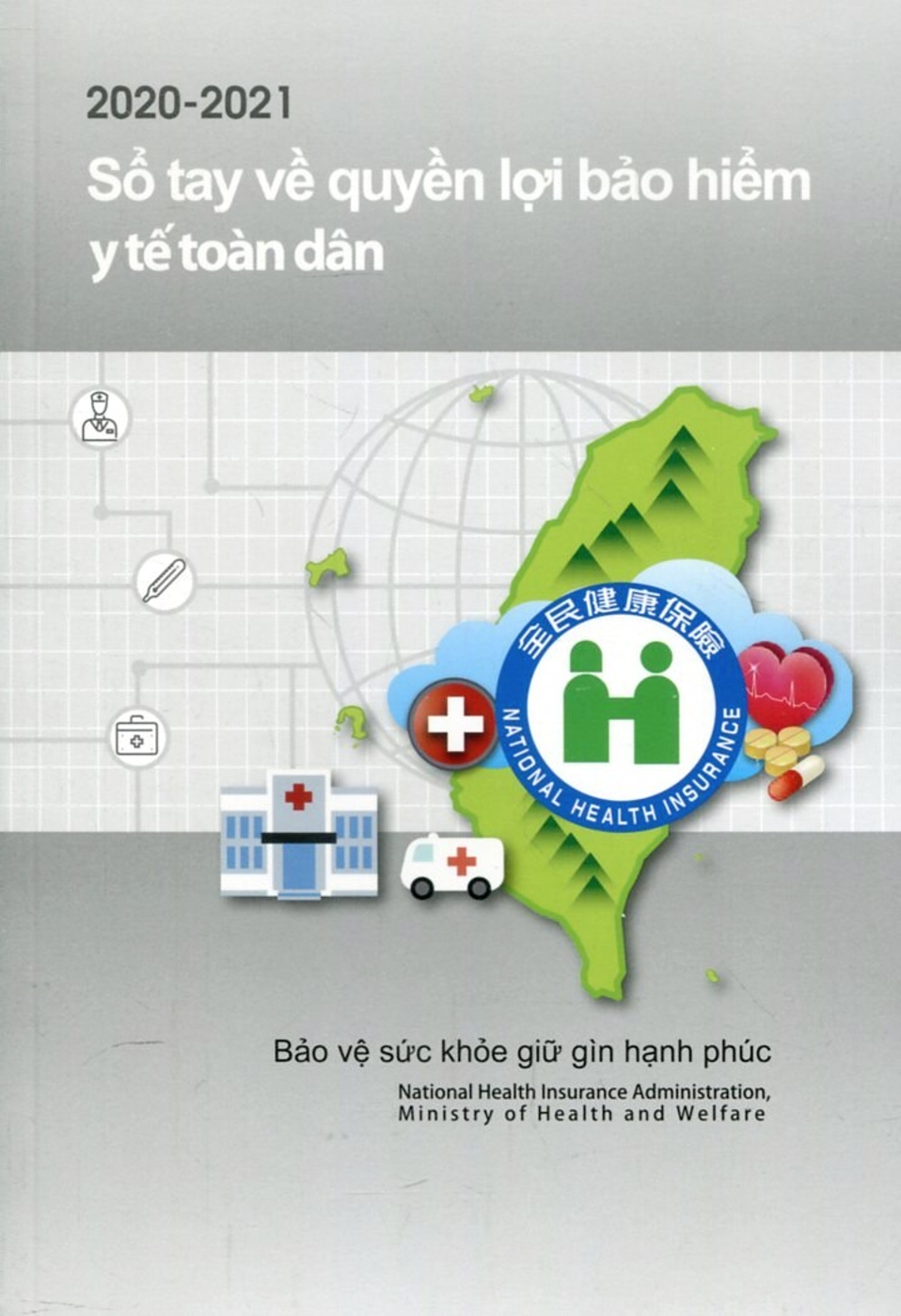 2020-2021全民健康保險民眾...
2020-2021全民健康保險民眾... 全民健康保險季刊NO.122(明年...
全民健康保險季刊NO.122(明年... 全民健康保險雙月刊NO.117-2...
全民健康保險雙月刊NO.117-2... 全民健康保險雙月刊NO.118-2...
全民健康保險雙月刊NO.118-2... 全民健康保險雙月刊NO.116-2...
全民健康保險雙月刊NO.116-2... 2015-2016 全民健康保險民...
2015-2016 全民健康保險民... 衛生行政與健康保險(2版)
衛生行政與健康保險(2版)